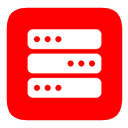随想云记 | 见证死亡与燃烧生命——写在夏目蓝的生日随笔
“我有一个请求,请在我之后死去,不要让我见证你的死亡了。”
我是一个非常畏惧死亡的人。这不是说,我畏惧死亡本身;相反,我很偏激的认为人在跨过某一个年龄开始,就从“无趣”→“有趣”的进化转向了“有趣”→“无趣”的衰退——我们宝贵而富有光泽的生命最好在这之前就结束。
死亡的人
我们的传统观念认为,一个人如果无疾而终(也就是不因意外、疾病等不可抗力因素死亡),这样的结局对他来说是“圆满”的。这样的观念还能引出一个推论,那就是在此基础上的让步条款:一个人如果因为意外、疾病等不可抗力因素死亡,但是在死亡的瞬间没有受到痛苦(或者痛苦持续时间很短),这样的结局对他来说也是“可以接受”的。
作为一个还算怕疼的人,我不可否认无痛/有限痛苦死亡确实是极具诱惑力的目标。然而,我总认为人在死亡前和死亡后能“做些什么”对我而言是更重要的目标。如果我在死亡前度过了我认为“有趣”的人生,又或是我死亡后的尸体能给世界带来一点不同和变化(用于医学或科学用途),是否完全无痛的死亡似乎就变成了无关紧要的事情。某种意义上来说,纠结究竟怎样死亡看起来总是一个很可笑的话题:因为无论舒服还是痛苦,在失去意识的那一刻开始,就和死者毫无关系了。(当然,相信灵魂和来世的唯心者会有别的解读)
小时候总觉得“燃烧生命”是一个很鸡血、很洗脑的概念;出于叛逆的目的,总是要用“生命高于一切”来反驳这个观点。在被王小波的有趣理论俘获之后,我开始思考燃烧生命的更多含义。对于一个死者来说,生前为之燃烧过的事业,是不是比死亡、死后都更重要的多呢?也许每个燃烧生命的人,都是抱着不同的心态、信念、目标去燃烧自己的,但是我乐观的相信,他们都有相似的逻辑链——在有限的生命消逝之前,尽可能绚烂、或是尽可能让世界绚烂。
我不希望做一个黯淡无光到最后纠结如何死亡这样细枝末节的无聊的人。
见证死亡
见证一个人的死亡永远是对生者的折磨:无论是愿意承认这一点的人,还是嘴上说着“他这也算是善终”了的自我安慰者。见证死亡和死亡最大的区别是,在见证了这世界对一个人类的最后折磨后,依然要带着这份记忆继续在这世界生存下去。对于许多身边的、亲近的人的死亡,我们见证的不仅仅是一个垂垂老矣的身躯离去;他/她在生前的勇敢、奋斗和一切美德都会在我们的脑海中再现——这是对人类一切美德的动摇甚至否定。
见证死亡是对生者的死亡预演。
他会持续的刺痛着正在“燃烧”的生者,提醒生者一切绚烂的最终归宿——这不免让一部分人心生畏缩,绚烂和渺小,最后的结局难道不是同样的、确定的吗?
完全正确,但是恰恰相反。正因为所有生命都会走向共同的结局,“燃烧”才给生存下了定义、作了注解、让生命不同于生命。说到底,我们不是为了最后那个共同的归宿而生存的:人总会走向死亡、器物总会走向损坏、甚至连宇宙也最终会走向热寂或坍缩,我们难道要假定人、器物、宇宙都没有意义吗?
某种意义上,人就是带着这样忽视了死亡的、近乎悲壮的信念,延续至今的。
于是我们能回过头来想到,那句在我们的小学、初中、高中被反复引用、甚至有些让人感到厌烦的话:“世界上只有一种真正的英雄主义,那就是在认清生活的真相后依然热爱生活。”
我会在见证了死亡之后,继续燃烧,这就是给生活的答案。
口是心非
即使做出了这样“懦弱”的宣言,蓝依然选择了在见证直哉“最后”的燃烧时目送他前行。因此,我总是认为她背负了和自我燃烧的人同等程度的痛苦;或者说,选择尊重并始终陪伴着这些自我燃烧的人,已经成为她对生活的答案、成为她的“燃烧”的一部分。
死亡的结局不会击垮那些甘愿燃烧自己的人。
.png?imageMogr2/format/webp)
在坎坷中前行的蓝,生日快乐。